内容
自 序
包康赟
文章合为时而著。本书能在2025年的春天面世,是它的幸运。六年前,中国第一次提出“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后续几年各个部门法都迎来了构建域外效力条款和域外适用制度的研究热潮。就在2024年7月,关于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中央文件首次在“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之后加上了“法治实施体系”。官方表述的变化不仅昭示着我国将逐步从涉外规则的制定阶段过渡至规则的实施阶段,也意味着学术研究的重点要逐渐从涉外法律的文本设计转向规则在域外的实际效果,而后者正是本书的研究对象。然而,中国的涉外法治建设终究会进入下一个阶段,与本书有关的法律现象和研究成果也必然会推陈出新——且看今年年初美国收敛了海外反腐败的势头,而欧盟的规则正在动摇域外企业的“加班文化”,这也意味着本书的内容和观点注定会过时。于是我就在思考:什么是蕴藏在这本小书中更具持久生命力的东西?或许有三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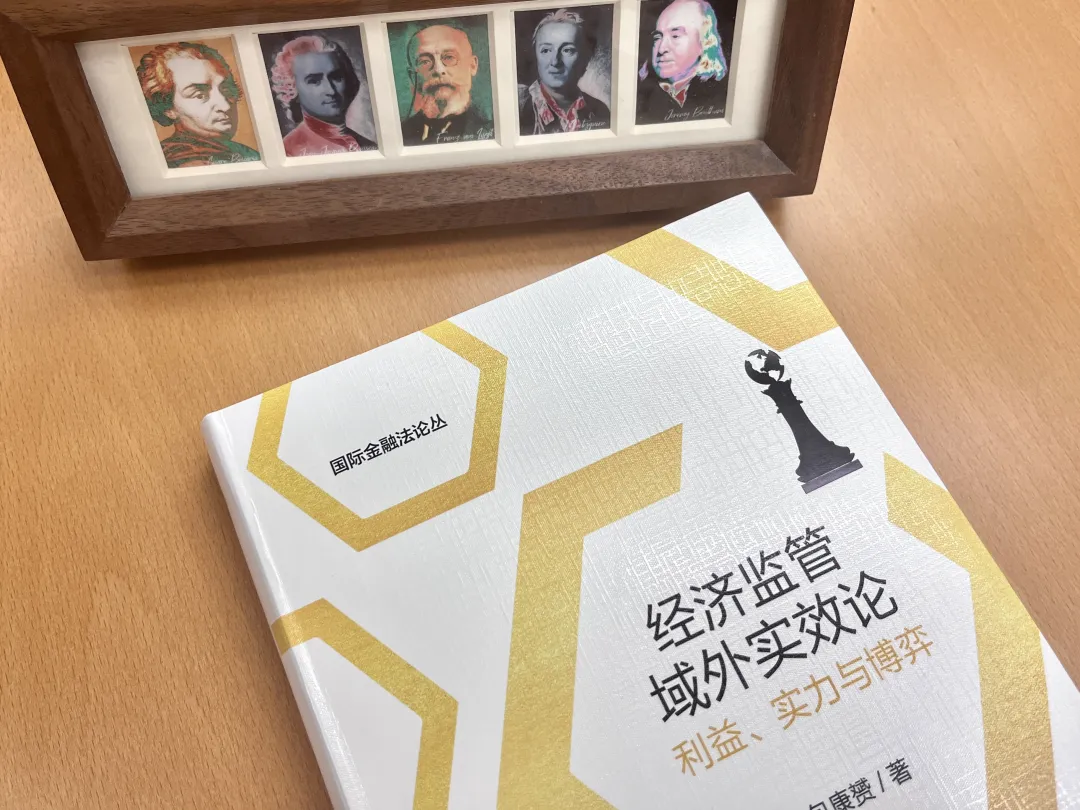
第一,融贯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决心。本书的专业属性虽然定位为国际经济法,实则探讨的却是国内法律规则。这并不是跑题。只要国家与国家不是一座座隔绝的孤岛,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界限就难以彻底划清。在国际经济法高歌猛进的岁月,我们时常看到国际规则在国内法上的回响甚至对照;而当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放缓脚步,国内规则将更多承担起涉外事务的处理工作。要知道国外法学院鲜有所谓的“国际经济法”专业,他们的国内法学者往往顺带着就将所行之处涉及的国际及涉外法律问题包揽了。在中国推进涉外法治的当下,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看到我国民商法学者在讨论CISG和国际保理、经济法学者在探讨外商投资法和关税制度,金融法学者的国际涉猎就更不用说了。国内法研究者在积极向“外”开拓,国际法学的自留地似乎越来越小。我并不是要唤起领地保卫战,只是想分享一些观察,而这背后很可能隐含着关于知识结构的一般规律。有法理学者曾打趣道,“与国内法相比,国际法简直就是小儿科了”,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秩序是早于国与国之间的。这么说有一定道理。我相信未来国际经济法领域想要不断发掘有意义的研究命题,产出更有深度和广度的研究成果,向“内”包容或许是光明的出路。
第二,对行动中的法律的好奇。我们总说法学是应用型学科,然而在法律学术圈,我们总需要有人专门站出来不厌其烦地解释“法学为什么需要一点实证研究”。这一点对国内法而言无比重要,对国际法就更是如此,因为在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或暴力机关保证规则的有效实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涉外和国际规则在实践中的运行情况尤其值得关注和反思。本书的研究对象重在“实效”二字,提出的“经济监管域外实效论”试图解释涉外经济规则产生实际效果的原因。诚然,研讨行动中的法律要从规范出发,但不能仅仅停留于规范本身,更无法只依靠法学内部视角下的方法和理论,而是需要调动一点社会科学的资源。这是因为从学科的比较优势来看,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乃至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相比于法学这一规范学科而言,更善于描摹现象和解释原因。无论是把法律作为自变量观察其影响,还是将法律作为因变量探讨其形成,都将深化我们对法律现象的认知,为规则的完善提供基础。
第三,探索普遍性道理的勇气。国际法学人对“提升话语权”的说法并不陌生。其实,在国际规则制定的议事厅和谈判桌之外,中国在学术研究方面话语权的提升也不容忽视。值得庆幸的是,学术圈的话语权并不总是以国家实力定声势高低,而是仍有机会以理服人,靠思想的力量不鼓自鸣。试想,如果我们的研究总是在重述外国法、总是致力于为本土问题提出地方性的方案,当这些研究被翻译成外文,是否能够吸引国际学友的驻足?能否让他们饶有兴致地听我们把话说完?我觉得希望渺茫。因为,他们似乎比我们更懂外国法,也大概率不会关心纯属中国的法律困境与应对。相反,如果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尽力揭示一些(哪怕是我们自己认为的)普遍性的道理,和国际学界真正交流起来,让他们也有智识的收获,那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法律是地方性的专业知识,但这不应成为我们自我封闭、满足于狭隘关切和局部影响的借口。我期待不限语言,越过领域和地域之后,我们中国法律人的学术研究仍有听众。对于这个宏大的目标,这本书是一次我个人的小小尝试。
本书的出版只是一个开端,我希望和读者一起带着决心、好奇和勇气,大步向前迈。
2025年3月于北京知春路

作者简介:包康赟,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法学和经济学双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美国耶鲁大学法学硕士、法律科学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为国际经济法、金融法、法经济学和法律实证研究。已在《法学家》《清华法学》《财经法学》、International Review of Law and Economics 和 The China Review 等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